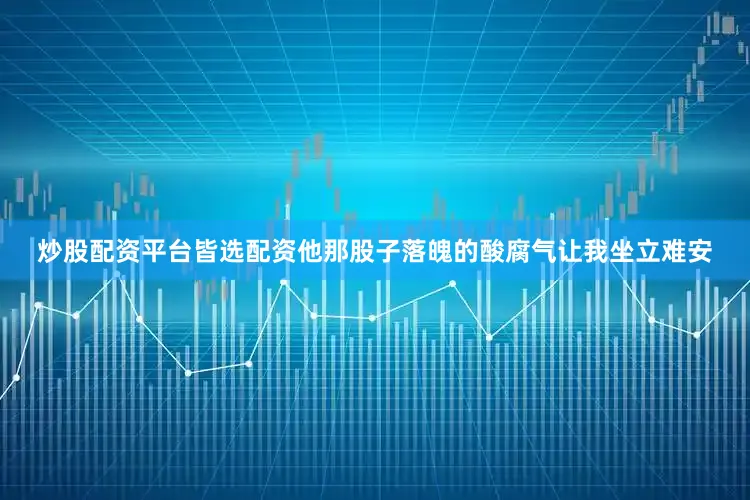
“这世上最贵的特产,从来不在服务区的柜台上。”老同学蹭我顺风车,竟在结账时买3000元特产暗示我付钱,我嫌恶避开,却在到家撕开包装的一刻彻底崩溃。三万块血汗钱与一张三十年前的救命借条,揭开了一场持续三载的卑微报恩。他为何宁愿背负骂名也要骗我离开?这背后到底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沉重?
【1】
二月的高速服务区,寒风卷着枯叶在水泥地上打转,刮在脸上像刀割一样疼。
我靠在奥迪A6的车门边,紧了紧大衣领子,目光厌烦地盯着休息厅。
那里,一个缩着肩膀、穿着件洗得发蓝的旧夹克的身影,正费力地拎着两个大礼盒走向收银台。
展开剩余91%那是老班,我大学时的班长。
半个月前,他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我回乡祭祖的消息,在同学群里私信我,说想蹭个顺风车。
一路上,他那股子落魄的酸腐气让我坐立难安。
他怀里死死抱着个油腻的编织袋,指甲缝里全是黑灰,甚至连呼吸都带着一种让人不适的沉重感。
“一共三千一百二十八块,先生,请问谁结账?”
收银台前,导购小姐的声音在寂静的休息厅里显得格外清亮,也格外讽刺。
老班站在那儿,两手局促地在裤缝上搓了又搓,然后慢慢转过头,眼神越过玻璃窗,直勾勾地望向我。
那一刻,他的眼神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卑微,又带着一种近乎偏执的期待。
我心里冷哼一声。
作为建筑公司的资深造价员,我这辈子最擅长的就是核算。
这种场景我见多了,典型的“社交绑架”。
从上车开始,他就在念叨现在日子难过,厂里效益差,身体也不行了。
现在,他竟然面不改色地挑了三千多块钱的顶级腊肉和山珍,却在付钱的时候看向我。
我嘴角勾起一抹职业化的弧度,那是生意场上最体面、也最冷漠的微笑:
“老班,这么多特产啊?行,你先结着,我去停车场把车挪一下,这儿位置窄,一会儿怕被人堵了。”
说完,我不等他那张局促的脸做出任何反应,直接拉开车门。
关门的一瞬间,我从后视镜里看到他像个被定住的木塑,收银员的白眼快要翻到了天上去。
我发动引擎,点燃了一根烟。
烟雾缭绕中,我觉得自己做了一个再正确不过的决定:
在我的世界里,老班这种人就是一笔“不良资产”,如果不及时止损,接下来的二十公里,他肯定会提出更过分的要求。
【2】
大约过了十五分钟,车门再次被拉开了。
老班拎着几个死沉死沉的袋子,气喘吁吁地挤进后座。
由于用力过猛,他剧烈地咳嗽起来,那声音像是破风箱在拉扯。
一股浓郁的、甚至透着点腥气的腊肉味瞬间占领了密闭的车厢。
“结完了?”
我扶着方向盘,头也没回,声音冷得像初冬的雨水。
“结……结完了。”
他嘿嘿一笑,一边顺着气,一边从兜里掏出一根皱巴巴的红梅烟递过来。
“周诚,刚才那特产……我挑了好久,真的,你别往心里去。”
我看着他指缝里那些怎么洗都洗不掉的工业机油黑灰,胃里翻腾了一下。
“车里不让抽烟,真皮座椅,烟味儿散不掉。”
我推开他的手,语气是不加掩饰的厌恶。
他愣了一下,赶紧把那根烟收回去,手僵在半空,尴尬地在膝盖上反复摩挲。
接下来的路程,我一言不发。
老班似乎察觉到了我的疏离,他尽量把那副嶙峋的身躯缩成小小的一团,紧紧贴着车门。
我们之间,隔着那道名为“阶级”的三十厘米。
那是我的体面与他的穷酸之间,最遥远的距离。
“咳咳……周诚,你爸走的时候,有没有留下什么心愿?”
他突然问了一句,声音沙哑得厉害。
我握着方向盘的手猛地紧了一下,父亲三年前因为肺癌去世,家里最难的时候,我也在群里发起过筹款。
那时候,老班作为班长,一个字都没回,更别提捐款。
现在他倒是装起深情来了。
“留了,他说做人得有自知之明,别给不相干的人添麻烦。”
我字字带刺。
老班的身子颤了一下,没再接话。
他转过头看向窗外飞速倒退的黑影,玻璃上映出他那张像枯树皮一样的脸。
【3】
离县城还有二十公里的那个三岔路口,老班突然提出要下车。
“就在这儿停吧,我……我想吃口老家的烩面,自己走回去就行。”
他指着那个黑漆漆、连个路灯都没有的路口,声音小得像蚊子叫。
我求之不得,直接一个急刹车靠在了路边。
“行,那你慢点,这路黑。”
我嘴上客套着,手已经按在了电子锁上。
老班费力地从后座爬出来,拎起那几个沉重的编织袋,却唯独把那个印着“顶级特产”字样的最大礼盒留在了座位上。
“拿走,东西落下了。”
我皱起眉头提醒他,心里一阵烦躁:难道还想让我送货上门?
他却像没听见一样,动作迅速地关上了车门。
隔着贴了深色膜的车窗,他突然对着我弯下了腰,深深地鞠了一个躬。
那个姿势保持了很久,久到我心里突然浮起一丝莫名的不安。
“周诚,谢谢你带我回家。”
他隔着玻璃喊了一声,声音在风中显得有些破碎。
“那特产……是我还给你爸的,一定要回家撕开看。”
说完,他拎着剩下的几个空袋子,深一脚浅一脚地扎进了路边的荒草丛里。
我看着那个在手电光下摇晃的、落魄得像乞丐一样的背影,冷嗤一声:
“还给我爸?三十年前的交情,也亏他好意思说出口。”
我一踩油门,奥迪A6咆哮着绝尘而去。
回到家时已是深夜,空荡荡的老宅里,只有父亲的遗像挂在正厅,眼神一如既往地温厚。
我把那个沉甸甸的礼盒随手扔在地上,心里盘算着明天就把这些东西拿去喂流浪狗。
可就在礼盒落地的一瞬间,盖子松开了,露出了里面包装粗糙的干肉。
而在那堆腊肉下面,我意外地摸到了一个硬硬的、被红色塑料布缠得死死的小方包。
我的呼吸在那一刻,戛然而止。
【4】
我发了疯似地撕开那个红色塑料包。
三叠厚厚的、带着体温和淡淡烟草味的百元大钞,像三块巨石一样砸在我的地砖上。
三万块。
在那些钱中间,夹着一张发黄的、连纸角都被磨圆了的借条。
上面的字迹是我父亲的,笔锋苍劲:
“今借予同乡班大国人民币一万元,用于救命手术,不设利息,不设期限,念及兄弟情深,不必挂心。周建国,一九九六年。”
而借条的背面,是一行歪歪斜斜、带着颤抖的字迹,那是老班写的:
“班子此命,周大哥所赐。三十年,未敢忘。今存够三万,连本带息,奉还周家后人。”
除了借条,还有一封用圆珠笔写的信,字迹已经因为汗水洇开了一大片。
“周诚兄弟,当你看到这些钱的时候,我可能已经躺在老家的土炕上了。
三十年前,我在矿下塌方,是你爸用脊梁撑住了那根横梁,把我背了出来。
那一万块钱,是全村人的救命钱,你爸却全给了我做手术。
后来你家落难,我在群里看到了,可那时候我正因为高压电工的职业病——尘肺病在住院。
我没钱,我真的没钱啊。
我没脸在群里说话,我怕我一开口,就会让你想起我爸欠你爸的那条命。
这三万块,一万是本金,两万是这些年我偷偷算好的利息。
我是个没本事的合同工,这钱,我存了整整五年。
在服务区,我故意让你厌恶我,故意让你觉得我贪财。
因为如果你真的给我结账了,我就没法把这钱‘演’进你的车里。
谢谢你给我留了最后一点尊严,没在收银台前拆穿我这个‘无赖’。
别找我了,我的肺像个漏风的风箱,快拉不动了。
把这钱拿回去,我这辈子,终于能挺直腰杆去见你爸了。”
我握着信纸的手剧烈颤抖着,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,大颗大颗地砸在那张磨损的借条上。
【5】.
我想起在服务区时,老班看向我时那个卑微到尘埃里的眼神。
他哪里是在索取?
他是在通过这种近乎自残的方式,确保我对他彻底失望,确保我会头也不回地“挪车”离开。
只有我走了,他才能把这用命攒下来的三万块钱,安安稳稳地留在后座。
他用最卑微的演技,成全了他作为一个报恩者最后的骄傲。
我疯了一样冲出家门,发动了那台昂贵的奥迪。
车轮在寂静的乡间小道上疯狂摩擦,发动机的嘶吼像是在嘲笑我的自以为是。
我一边狂踩油门,一边颤抖着拨打老班的电话。
关机。关机。还是关机。
我托人连夜查老班的消息,最后得到的回复,像是一记重锤击碎了我的头盖骨。
“周诚,你找班子?他半年前就辞职了,为了拿那笔两万块的伤残补助。他肺坏死,医生说手术没意义了。他把剩下的积蓄都留给了家里,只带了三万块现金说要出门办桩‘天大的事’。”
我的手死死扣住方向盘,由于用力过猛,指关节白得惊人。
三万块,那是他的命,是他用最后一点呼吸换回来的自尊。
我在那个黑漆漆的岔路口停下,拿着强光手电在荒草堆里疯狂地搜索。
“老班!班长!”
除了夜枭的惨叫,只有风声在回应我。
突然,手电的光柱扫到了草丛里一个亮闪闪的东西。
我连滚带爬地跑过去,那是他在车上想递给我、却被我嫌恶拒绝的那根红梅烟。
由于被露水浸透,烟卷已经散开了,露出里面一根坚硬的塑料管。
我撕开那根细小的管子,里面藏着一张卷得极细的纸条,只有四个字:
“多吃蔬菜。”
那是我父亲生前最爱挂在嘴边的一句老话。
老班,他竟然记了三十年。
【6】
我终究还是没能在老班断气前赶到他身边。
当我找到他的家时,院子里已经搭起了灵棚。
他老婆坐在门槛上,手里攥着那个装特产的塑料袋,哭得已经发不出声了。
“他最后一口气的时候,一直盯着门口看。”
她把一个布包塞进我手里,里面是他在特产店付钱后的找零。
“他说,他在服务区演得挺像,没让你看出破绽。他说,他这辈子最后悔的事,就是没能在你爸走的时候,亲手送上一束花。”
我拆开那个布包,里面只有一张揉皱的、价值三十一块钱的慢车票。
那是他给自己留的、回村治病的最后一点钱。
而在那个服务区的收银台前,他拎着三千块钱的腊肉看我时,他的兜里其实已经空得连一张返程的车票都快买不起了。
我站在灵堂前,看着遗像里那个黑瘦的男人。
我是一个造价员,我能精确计算出每一平米混凝土的价格。
但我却算不出,一个落魄灵魂的厚度,到底能承受多少公斤的愧疚。
【7】
一周后,我卖掉了那台象征身份的奥迪A6。
每当我想起那三十厘米的社交距离,想起我那个自以为是的、躲避社交绑架的微笑,我就觉得浑身冷得发抖。
现在的我,换了一辆最普通的国产车。
我把那三万块钱,加上我这几年的奖金,凑了五十万,以老班的名义捐给了县里的一所希望小学。
学校落成那天,我没去剪彩,只是远远地看着那些孩子。
我总觉得,在那群孩子清澈的眼神里,藏着老班最后那个鞠躬的影子。
我开始关注那些在群里沉默的人。
我开始明白,这世上有一种卑微,是因为背负了太重的信义;
有一种落魄,是为了守住最后的干净。
【8】
清明节,我再次回到了那个三岔路口。
我在路边点燃了一堆火,把那张发黄的借条慢慢放进了火光里。
纸灰随着山风盘旋,越飞越高。
在那迷蒙的灰烬中,我仿佛看到了三十年前的那个矿井。
我的父亲背着年轻的老班,从废墟里一步一步爬向光明。
而三十年后的今天,老班背着那沉重的三万块,从我的偏见里一步一步爬向了永恒。
我整理了一下衣服,对着空旷的原野深深鞠了一躬。
债清了。
天真的亮了。
发布于:湖北省配查查-炒股配资平台选-正规配资论坛-专业股票配资价格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- 上一篇:可靠的配资门户 评分更是稳居春节档前列
- 下一篇:没有了



